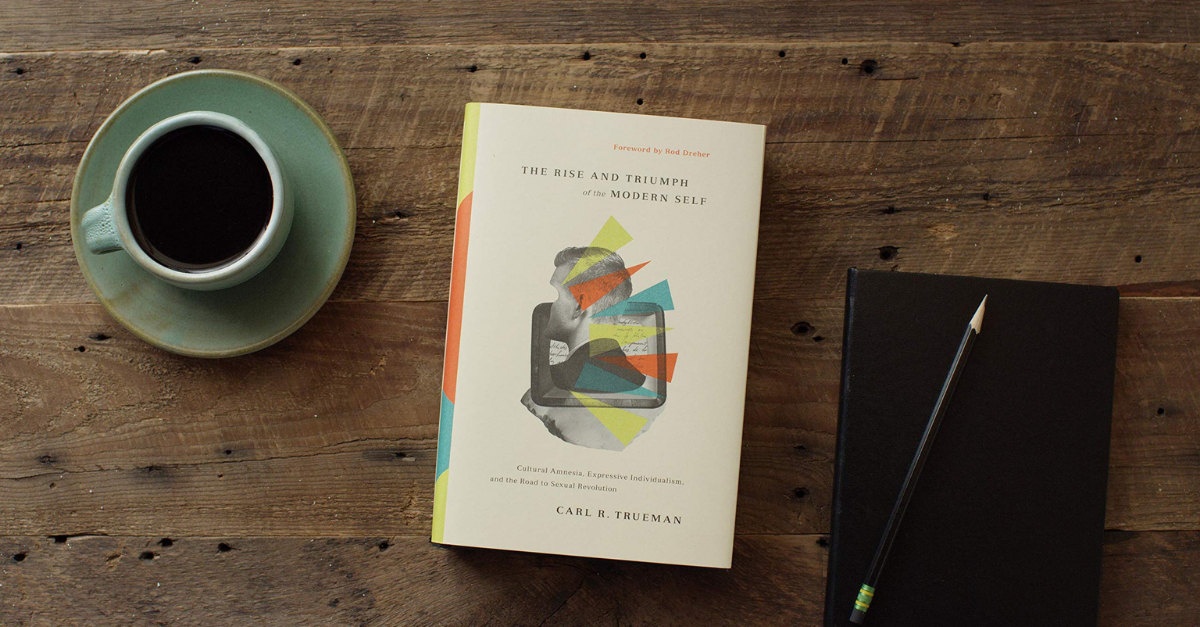
華盛頓·歐文(Washington Irving)寫過一個奇幻的故事,講述了一個怕老婆、不愛工作的男人,名叫瑞普·範·溫克爾(Rip Van Winkle)。該故事發表於 1819 年,背景是 18 世紀末的美國,講述了瑞普在紐約的卡茨基爾山獵松鼠時躺在地上。他喝得昏昏沉沉,陷入沉睡。20 年後他醒來,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睡了不止一個晚上。
一些跡象表明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的鬍子有一英尺長,他的狗不見了,他的步槍上佈滿了鐵鏽。當他走進他的村莊時,他都不認識他了。有些建築他不記得了。他的衣服看起來很老式。孩子們取笑他。瑞普宣稱自己是喬治三世國王的忠實臣民,但他沒有意識到,在他睡著的時候發生了獨立戰爭,美國現在是獨立的國家了。他覺得很不適應,卻不知道爲什麼。
今天許多基督徒都有類似的經歷。他們雖然沒有在身體上沉睡 20 年,但他們可能一直被包裹在一個基督教的小泡沫中,這個泡沫由主日聚會、基督教大會、基督教書籍和基督教音樂組成。他們一直與世俗社會絕緣,並與之脫節。現在他們開始醒悟過來,意識到世界已經改變,事情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繼續下去了。
過去,世人認爲基督徒是有些古怪的,但基本上是正派的人士。而現在,我們越來越被別人看作是社會中的有害勢力。我們現在是「壞人。」[1] 像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這樣的東西曾經被視爲絕對的權利。現在它們則面臨挑戰。你可能因爲表達某些觀點而失去工作,特別是關於性別和婚姻等問題的合乎聖經的觀點。社會發生了劇變——可能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而且在好轉之前,情況很可能會變得更差。
卡爾·楚曼(Carl Trueman)用一個例子來說明事情到底發生了多大的變化,他在關於這個主題的這本里程碑式著作的一開始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我是一個被困在男人身體裡的女人」這句話怎麼就在當今社會變得有說服力和意義了呢。[2] 我們的祖輩聽到這樣的說法一定會感到難以置信。但現在,整個社會都認爲需要認真對待這句話。到底發生了什麼?
楚曼的《現代自我的崛起與得勝》是迄今爲止對我們的現狀最徹底、最有幫助的介紹。然而,它有 400 多頁的深入思考和嚴密論證。許多忙碌的牧師根本沒有時間去讀。
所以,我想給出我自己的合乎聖經的簡介,並試圖勾勒出楚曼作品的概要。我的目的是讓我們思考,希望牧師們能夠就這一現狀向神的子民提供容易明白的教導。畢竟,這不僅僅是一段引人入勝的當代歷史;它更是很可能導致忠心的基督徒失去朋友、甚至生計的東西。
許多關於性和可接受的性行爲的文化規範已經遭到了掃地出門。特別是,基督教對性別和婚姻的觀念被認爲是壓迫性和損害性的而受到拒絕(創 1:27;太 19:4-5)。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首先,我們需要從聖經出發來理解這一點。這種地震般的轉變並非憑空而來,也沒有出乎聖經中這位神的預料。
當神遭到拒絕時會發生什麼?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裡,世俗思想家認爲,神要麼不存在,要麼至少與日常生活無關。我們完全可以把他排除在外,而幾乎不會有什麼變化。但聖經並不是這樣說。轉離神會在最深的層面上影響一個社會。我們應該明白,這正是我們現在目睹之鉅變的根源。
我將查考新約中的兩段關鍵經文。
第一段,是保羅給以弗所教會的話(弗 4:18–19):
他們(那些不信神的人)心地昏昧,與神所賜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
這些經文闡明了那些生命中沒有神的人走向享樂主義的軌跡。他們對於神和屬靈之事「良心既然喪盡」,就用私慾來填補心中的空虛。他們「放縱」肉體的享樂。保羅指出,這會使他們走向非法的性行爲,並走向極端。這就是我們現在的情形。
也想一想保羅對羅馬教會所說的話(羅 1:18–32):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因爲神已經給他們顯明。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因爲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爲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稱爲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爲偶像,彷佛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體。……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爲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
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請注意兩段經文的相似之處。保羅談到那些「放縱」(give themselves over)情慾的人,但我們也讀到「神任憑他們」放縱(God gave them over)罪惡的慾望,以表達他對於他們否認他的忿怒。社會否認神時,是不會保持不變的。它往往會變得性化,而且這種變化會非常迅猛地發生。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我們當前的文化。在某種程度上說,楚曼的書只是在現代歷史中追溯了這些經文所指出的軌跡。西方世界曾經被認爲是「基督王國」(Christendom),但它現在已經被性和性政治所主導。當然,放縱派一直都有。但現在他們的觀念主導了文化。多個世紀以來,基督教的道德觀和家庭觀一直是西方社會的基石。但現在,這種觀念正在遭到推翻。
因此,在本文中,我們將嘗試總結楚曼的著作,說明這種情況是如何已經發生並且正在發生的,並指出他的一些結論。
預備性觀念
在我們進入論證之前,要先講一些預備觀念,這些觀念是楚曼從其他現代思想家那裡借來並引用的。
仿效和生造(Mimesis and Poiesis)
以下是楚曼對這些術語的定義:
簡單地說,這些術語指的是兩種不同的思考世界的方式。仿效的觀點認爲,世界有既定的秩序和意義,並因此認爲人類需要發現這種意義並使自己符合它。相比之下,生造的觀點視世界爲大量的原材料,個人可以從中創造出意義和目的。[3]
壓制創造主神的真理,選擇不承認神,就會讓我們走向生造。我們把世界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沒有人告訴我們該怎麼做。作爲基督徒,我們瞭解罪和墮落的人性中固有的反叛本性,因而我們可以理解爲什麼人們會自然地偏愛生造而不是仿效。
三種類型的世界
美國社會學家菲利普·雷夫(Phillip Reiff)有一個相關的想法。他從三種類型的世界來談這個問題。
「第一型世界」是異教世界,其道德準則基於社會普遍接受的神話。「第二型世界」是那些建立在對其上帝的信仰之上的世界。因此,第一和第二型世界都有一個建立在人以外的超然事物上的道德觀。這爲這些社會提供了穩定性的一種來源。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第三型世界」的道德要求並不以任何神聖事物爲基礎。沒有任何事或人在他們自己之上。他們根據自我來判定自己和自己的行爲是正當的。拒絕神會使我們進入雷夫所說的第三型世界。
事實上,雷夫給這種第三型世界貼上了「反文化」的標籤,因爲這類文化認爲第一和第二型世界的文明和道德框架是對個人自由的壓迫和限制。第三型世界故意試圖通過雷夫所說的「死亡作品(deathworks)」來顛覆和破壞第一和第二型世界的文化規範。這些事情以冷嘲熱諷的方式使舊有的價值觀顯得無能和可笑。例如,這是色情作品的一個主要方面。它不僅宣揚情慾,把人當作純粹的「東西」,而且還否定了任何認爲性在行爲本身的快感之外還有任何意義的觀念。神和那些想要限制這種快活的人只不過是假正經的快樂屠夫。
用雷夫的話說,我們現在生活在第三型世界,或者至少處於第三型世界的邊緣。
把神排除在外已經重塑了人們現在對自己和他人的看法。楚曼寫道:
其基礎論點是,性革命及其在現代社會的種種表現,不能被孤立地對待,而必須被解釋爲一個要深廣得多的革命的具體的、也許是最明顯的社會表現,這個革命關乎對於自我意義的理解。[4]
自我的軌跡
楚曼採用了一些標籤來總結自我的歷史發展路徑。「心理的自我」之後是「浪漫的自我」。繼而是「可塑(或易塑)的自我。」接下來是明確的「性自我」,而在新左派的論點中,它現在已經成爲了「性政治化的自我」。這是我對他的論點的改述。我將在下面逐一解釋。
所有這些都與我們可能提出的合乎聖經的自我觀大相徑庭,按照聖經,自我是按照神的形像創造的,墮落了,但也得了救贖。基督徒的自我觀是一種向外看的自我。我們仰望神和基督來尋找我們的意義和身份。但現代自我已經轉向內向。
心理的自我
當我們離開宗教改革思想進入18世紀啓蒙運動時期時,我們的第一站是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 年)。在盧梭看來,人在被社會力量腐蝕之前,本性上是善的。根據盧梭的說法,一個人的真正身份是在他或她的內在心理自傳中找到的。[5] 盧梭在談到他的《懺悔錄》時寫道:「我承諾的是我的靈魂的歷史,爲了忠實地講述它,我不需要其他的備忘錄;我所需要做的一切就是審視自己的內心,就像我迄今爲止所做的那樣。」
隨之而來的是對自愛,[6] 共情和同情的強調,認爲它們是良心的主要信息源以及個人與腐敗社會之間的張力關係。楚曼評論道,「在盧梭的觀點中,我們可以看到現代表現型個人主義的基本輪廓浮現出來。」
浪漫的自我
18 世紀末和 19 世紀初的詩人——華茲沃斯(Wordsworth)、布萊克(Blake)和雪萊(Shelley)——將盧梭的思想從知識精英那裡拿出來,並將其普及到主流文化中。盧梭關於社會在腐蝕和殘害無辜個人的觀點在工業革命的時代似乎很常見。解決辦法就是向內轉,並回到理想化的田園生活。
楚曼說,「華茲沃斯和雪萊都表達了關於詩歌的觀點,認爲必須在詩意美學和倫理學之間建立明確的關聯。」對這些浪漫主義者來說,真正的道德是關於感覺正確和看起來正確的事情。一旦你的目光離開了外在的參照系,所有的「道德」判斷往往就變成了個人偏好或感受的表達。我們進入了一種「療癒 文化」。這對性倫理有重大影響。作爲一個人的真實性就是對自己的慾望不感到羞恥,並隨欲而行。[7] 顯然,這種思想爲當今發生的許多事情提供了基礎。
可塑的自我
可塑的人不僅是心理的人。用楚曼的話說,他是「一個認爲自己可以隨意製造和重塑個人身份的人。」[8]
這種思想的基礎是哲學家弗雷德里希·尼采(1844-1900 年)和卡爾·馬克思(1818-1883 年)以及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1809-1882)奠定的。尼采因其冷峻的無神論而聞名,他將生活視爲權力鬥爭,並邀請我們超越人性而成爲超人(Ubermench)。馬克思認爲工業生產和資本主義不僅改變了社會,而且重塑了人們自身以及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因此,人的本性是可塑或易塑的。人的本性不僅僅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它不是固定的。
達爾文對人類起源的解釋強化了這一點。人們必須接受,他們只是進化的偶然產物,因而並不是爲了實現任何命定之事而造的。他模糊了人類與動物之間的界限,並消除了任何人類具有特殊地位的觀念。我們是不斷進化的。我們是可塑的。
性自我
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年)是這個故事中的關鍵人物。他把幸福等同於「生殖器快樂」。從那時起,個人身份就與性和性取向等同起來。現在這種觀念主導了西方世界——所以,人們根據他們的性慾被分類: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等等。對許多人來說,這是關於他們是誰的最重要真理。
如果對盧梭來說,自然人是無辜的,那麼對弗洛伊德來說,人類的潛意識就是黑暗、暴力和非理性的。精神分析學家的工作就是挖掘在我們內心中存在的看不見的力量,並將它們帶到意識的表層。有趣的是,精神分析的靈感來自古典神話(俄狄浦斯情結等)[9]。在他的《自拍》一書中,威爾·斯托爾(Will Storr)引用了一位專家的話:「沒有古希臘的神話……就沒有精神分析。」[10]
弗洛伊德將性衝動置於人之爲人的核心。[11] 在弗洛伊德以前,性是爲了繁衍和快樂(箴 5:19)。現在它們變成我們的真實身份了。最幸福的人是能夠不斷放縱自己性慾的人。然而,這正中了有權勢之人的下懷,所以我們需要文明來抵制這個。因此從弗洛伊德的角度來看,根據楚曼的說法,「這意味著文明人不可能真正幸福。」[12]
性政治化後的自我
弗洛伊德的思想後來被用來改變對壓迫的經典理解。這是故事中的另一關鍵步驟。
因爲身份關乎我們的內在自我,尤其是我們的性慾,所以受害者身份就被心理化了。那種認爲壓迫是關乎貧窮或身體虐待的觀點已經黯然失色。既然是這樣,那些感到無法表達自己的性慾,或其性慾被社會視爲不可接受的人,才是被壓迫的。壓迫是關乎情感的。
性不再是一種私人活動,因爲它關係到我們的社會身份。例如,取締或僅僅容忍同性性行爲,就是取締或僅僅容忍某種身份。它觸及了一個人認爲自己是誰的核心之處。
許多大學的人文學科都接受了所謂的「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13]。結果,他們都緊緊抓住了這種對受害者和壓迫的新理解。新左派將傳統的性規範解釋爲爲維持社會現狀而採取的惡毒策略。因此,西方的理想必須被推翻。按照這種理解,家庭是專制國家的縮影。因此,現在一些人認爲,廢除家庭對於政治解放至關重要。
性革命則是實現這一目的的途徑。而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 年)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議題。像寬容這樣的價值觀是一種假象,只不過是安撫人們接受男權的、資本主義的權力結構的一種方式。這場鬥爭必須針對那些教導寬容的教育機構。
身份與團體
對內心幸福和心理健康的渴望是現代的核心所在。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現在人們普遍接受的是,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你的內在形像就是真實的你。這甚至優先於一個人的身體,[14] 這就開啓了你的生理性別(biological sex)和你的性別(gender)之間存在差異的可能性。你認爲自己是誰才是你的真實身份,不管你是有 XX 還是 XY 染色體。因此有了「我是一個被困在男人身體裡的女人」這種說法。現在它還「有道理」了。
然而一個人的身份要得以顯揚,就必須得到他人的認可。用專門術語來說就是,身份是對話性的;換言之,它依賴於只有通過與他人的互動才能發展出來的語言。
因爲我們是關係的存在,我們需要他人的接納才能讓自己感到舒服。這意味著,社會必須服務於滿足個人心理需求的目的。這就創造了治療文化,所有的機構和團體(包括教會)都必須適應這種文化,以反映治療和包容的心態。
楚曼對此進行了反思:
任何個人拒絕承認被整個社會承認爲合法的身份,都是一種道德上的冒犯,而不僅僅是冷漠的問題。現代世界的身份問題就是尊嚴的問題。出於這個原因,美國關於爲同性戀婚禮提供蛋糕和鮮花的各種法庭判例,最根本上並不是關於鮮花或蛋糕的。它們關乎對同性戀身份的認可,而且根據 LGBTQ+ 群體成員的說法,他們需要得到這種認可,才能感到自己是社會的平等成員。[15]
這解釋了爲什麼忠心的教會不可能被簡單地置之不理。聖經在當前世俗意識形態不希望有界限的地方劃出了界限。就像我們都失敗的許多其他事情一樣,同性相吸和性別混淆違背了神的美好創造。因此,從長遠來看,它不會導致個人或社會的繁榮。
性和性取向問題現在主導了西方世界。
在他的書中,楚曼最根本上突出了三個「得勝」:色情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無處不在;特別關鍵的法律決定現在如何在情感主義和美學的基礎上做出;以及跨性別主義如何在社會中取得進展。
色情主義
從電視肥皂劇到青少年流行音樂,我們的文化現在已經充斥著性主題。
色情作品的盛行尤其值得注意。當然,科技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如果自由和幸福被囊括在性滿足中,那麼網絡色情就成爲顯而易見、最容易、和最私密的(似乎)解放和滿足的媒介。色情作品是性革命的縮影,因爲它把性表現爲純粹的娛樂——一種身體上的、讓人愉悅的行爲,與任何更大的關係性意義或超越性脫鉤。它使性與任何倫理背景分離開來。[16]
而且,人們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色情作品不再被視爲男性統治和暴力侵害女性的例子。甚至還有人談論「有道德來源的」色情作品,其中女性不會被強迫參與,並且「表演者的權利」受到了尊重。楚曼寫道:
我在這裡提出的哲學主張是,主流文化中色情作品的正常化與主流文化對神聖秩序的抗拒有著深刻的聯繫。色情作品帶有一種關於性以及人類意義的哲學,這種哲學與傳統的宗教觀點背道而馳,在西方這種傳統觀點主要是基督教。因此,它既是在現代出現的去創造、去神聖化的世界的症狀,也是其構成部分,它起源於盧梭和浪漫主義,並在馬克思、尼采、達爾文、弗洛伊德和新左派採用的哲學和科學術語中得到了鮮明的表達。色情作品的得勝既是神之死的證據,也是殺死神的手段之一。[17]
換言之,色情作品是一種「死亡作品」。一些社會學研究表明,色情作品的使用和對傳統宗教信仰的拒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聯繫,尤其是在青少年中。
治療學
在他的著作中,楚曼早些時候提到了哲學家阿拉斯代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和他的著作《美德之後》(After Virtue),該書認爲現代道德理論無法解釋道德規範的理性權威。而現代道德理論的失敗所留下的空白,已經由麥金泰爾所說的「情感主義」填補,在其中,所有的評價性和道德性判斷都「只不過是態度或感覺上的偏好的表達。」這與浪漫主義詩人很像。楚曼又說,「本質上,情感主義把偏好當作是真理的主張來呈現。」[18] 這就是法庭上的治療文化。正如我們前面所看到的,社會機構必須進行調整,以促進個人的心理健康。這件事現在已經進入了司法領域。
在評論奧伯格菲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最高法院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案件)時,楚曼說,案件中所使用的倫理邏輯不過是與性化的治療文化態度相符的情感主義。關於這個判決,他寫道:
這是情感主義。傳統中那些支持當代品味的部分是觀點正確性的有力證明;而那些對支持想要的結論沒有用處,或與當代品味衝突的部分則可以被視爲過時的或是出於偏執的動機,或者乾脆直接忽略。法院可以放心地這樣做,因爲它正向著整個社會說話,而這個社會恰恰就是以這種方式思考的。該裁決及其支持性論證絕對與我們之前……所追溯的思想轉變有關,並依賴於這些轉變,這些思想轉變關乎自我、人性、性取向以及壓迫和自由的本質。[19]
跨性別主義
現在,身份被人從一種自我的角度來看待,這種自我是心理化的、性化的,並且能夠創造和重新創造自身。這就爲那種觀念鋪平了道路,即一個人認爲自己一種性別、卻被困在另一種性別的身體裡,或者不再希望被歸類爲男性或女性。在一個將心理置於生理之上的社會中,這樣的觀念是邏輯一致的。
LGBTQ+ 聯盟共同反對社會的傳統性規範。跨性別者與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者結成共同的事業,因爲他們將異性戀規範視爲共同的敵人。然而這個聯盟也沒那麼容易團結一致。這裡面存在著矛盾。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都稱自己是被同性吸引的男人和女人。但這是以固定性別爲前提的。那些主張跨性別以及走得更遠的人不接受固定性別的觀念。他們認爲性別是一個流動的概念。
跨性別女性(男變女)的地位在爲婦女權利而戰的老一輩女權主義者中引起了激烈的爭議。經典女權主義者認爲,作爲女性的整體地位被跨性別者主義所破壞和非政治化了。很多人覺得,你不能把女性和女性歷史以及作爲女性的身體成長經歷分開。但正如楚曼所指出的,「作女人現在可以通過技術來實現——實際上就是由醫生開張處方的事。」[20]
跨性別主義似乎否定了身體對自我的重要性,而這意味著對父母的否定——就是那些懷孕、生下和撫養小女孩或男孩的人。楚曼引用傑梅茵·格里爾(Germaine Greer)的話說:「不管它是什麼,變性都是對母親的驅魔。」[21]
當我們逐步接受了對性革命和我們現在生活的這世界的描述時,我們應該意識到,並非所有發生的事情都是壞事。有兩件事基督徒最好特別注意。
首先是尊嚴。楚曼寫道:「隨著盧梭對個人和作爲理想的自然狀態的強調,向個人內在尊嚴的轉變非常明顯。而這是基督徒應該贊同的事情。我們不應該把窮人的生命價值看得比富人或重要的公眾人物低。」[22] 不幸的是,這種對尊嚴的重新強調與任何神聖的秩序並不相干。它不是以所有人都是按神的形像創造的這一真理爲根基的(雅 3:9)。
第二是真實性。雖然楚曼沒有這樣說,但性革命希望人們裡外一致的關注確實在新約中能找到積極的回應——不是以一種罪惡的方式,而是以一種敬虔的方式。耶穌登山寶訓的一個重要主題是真實性,即敬虔的行爲必須發自內心的信念(太 5:27–28,6:1)。
但一般而言,基督徒需要極爲警惕和有分辨。
處理 LGBTQ+ 問題
基督徒需要謹防簡單地接受這個世界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方式。教會在性倫理方面的教導是否應該在世人面前顯得「合理」?當然不是。我們的工作是愛所有人,同時保守對神的忠信。
這世界所使用的範疇具有誤導性,而我們很容易陷入其中。若是這樣,我們便失去了對關鍵問題的清晰認識。認爲我們的真實身份是性的觀念是錯誤的。創世記的記載告訴我們,性是我們所是中的一個功能,而不是我們的所是(創 1:27–28)。亞當在和夏娃發生性關係之前,就是一個真正的人。
如果這個世界的範疇建立在一個基本的範疇錯誤(性慾就是身份)之上,那麼基督徒就不應該簡單地讓自己在這個 LGBTQ+ 的框架內被定義。認同這些範疇就會認同其論證。楚曼寫道:「在更廣泛社會中的身份框架是根深蒂固的、強大的,並且與聖經中作爲基本範疇所提倡的那種身份是根本對立的。」[23]
性道德
性革命建立在這樣一種觀念上:性只是爲了取樂。不幸的是,「自由做愛」的後果很大程度上通過墮胎和藥物得以避免。但更深層次的困難已經開始出現。
首先,正如弗洛伊德所預見的那樣,「自由做愛」的方式有利於強者。「#我也是」(#MeToo)運動正確地揭露了這一點。這世界認識到了這些事情的可怕之處。
第二,在性革命下,人們想要的是,在「同意的成年人」之間發生性行爲是可以接受的。但正如許多法庭案件所發現的那樣,定義什麼是同意非常困難。一方認爲是同意的,另一方卻不這麼認爲。即使就其本身而言,這也要求把性置於道德框架內。當然了,這是性革命最不想做的事情。
同性戀婚姻
在《舞會之後:美國將如何克服對同性戀的恐懼和仇恨》(After the Ball: How America Will Conquer Its Fear and Hatred of Gays)一書中,神經心理學家馬歇爾·柯克(Marshall Kirk)和廣告經理亨特·馬德斯(Hunter Madse)建議同性戀群體,如果它想要得到接受,就需要塑造一種更可愛、更萌的自我形像。同性戀婚姻現在已經來到,並且所有的治療性言論和形像都站了在它一邊。它看起來會一直存在,所以忠心的基督徒將需要思考如何應對和解決這一事實。
爲了能容得下它,婚姻不得不重新定義,而有可能它的弱點將會是婚姻被重新定義的方式。也許立法已經爲其他形式的「婚姻」打開了大門,而這些「婚姻」對西方大眾來說最後並不那麼有吸引力。例如,它是否會使一夫多妻制成爲可能,而這很可能導致對婦女的不公平對待和虐待?
當我們將同性婚姻與跨性別主義混合在一起時,會出現更多的問題。楚曼講述了一個女同性戀婚姻的故事,其中的一個女人變成了男人。這讓她的伴侶完全困惑了。她不知道她是誰。她是一個嫁給男人的「直(straight,即:異性戀)」妻嗎?但如果她是一個女同性戀,那麼爲什麼她要嫁給一個男人呢?
宗教自由
聯合國在其《世界人權宣言》第 18 段中,保障了宗教自由和改變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性革命的表現型個人主義正在給宗教自由帶來壓力。
在西方,委身宗教的人數的普遍下降,尤其是年輕人的流失,意味著社會對宗教自由不太關心。信仰人群和基督徒的自由很容易受到限制,甚至最終被剝奪。在西方,目前人們認爲性慾是個人身份的關鍵,因此也是每個人尊嚴的關鍵。這壓過了宗教自由,意味著社會認爲沒有教會可能還更好。
教會應當如何回應?一些保守的福音派人士只是繼續走他們的老路,希望我們所討論的事情會簡單地消失或者繞過他們。這是不太可能的。另有的教會對聖經中關於性道德的明確教導做出了妥協,或者至少試圖製造一些「迴旋餘地」。
每個牧師都需要謙卑地打開他的聖經。他需要祈求智慧,好知道該如何在現今這時代帶領教會。這裡有三個建議。
合乎聖經的身份
明確地說,當一個年輕男子來到他的牧師面前說,「我想我是同性戀」,或者一個女孩私下向她的母親承認,「我想我可能是一個女同性戀」時,第一反應應該是充滿愛心地說,「你之所是遠超乎你現在受到的性誘惑。」當代世界將人們縮小到他們的荷爾蒙上。但人之所是極有榮光,遠超乎單純的性愛機器。人類在科學、藝術和人道主義方面的整個成就史都在房頂上宣揚這件事。我們是「神所生的」(徒 17:28)。所以,牧師啊,我們的講道必須幫助人們擺脫瑣碎化的肉慾人性的醜陋、孤立的禁錮。人性正在被毀滅,而我們蒙召是要拯救它。
對與錯
當人們「愛自己」時,則好的東西往往被認爲是「讓人感覺良好」的東西,而壞的東西往往被認爲只是「讓人感覺不好」的東西。教會很容易陷入這種思維方式,因爲讓人立即感覺好起來顯得很有愛心。
但即使是常識也告訴我們,這過於簡單化了。化療不會讓患者感覺良好,而是極爲難受,至少開始時是這樣的。從屬靈的角度講,認罪不是一種好的感受,但它確實能讓我們看到我們需要基督並他釘十字架(徒 2:37)。楚曼寫道:
教會應該對美學與她的核心信念和實踐之間的關係進行長期而仔細的反思。我在上面指出,今天的倫理講論的標誌之一,是它對個人敘事的依賴。……個人敘事被呈現爲不容置疑的,正是因爲它們是個人的見證——而這是表現型個人主義的時代中的最高權威形式。這種對美學的關注反映了同情心和同理心在塑造道德方面的恆久力量。……教會需要對這種基於美學的邏輯做出回應,但首先她需要清醒地意識到這一點。而這意味著她本人必須斷了這樣的念頭,就是沉迷於更廣泛文化中的那種美學策略,並從而使其合法化。教會內部關於 LGBTQ+ 問題的辯論必須根據道德原則來決定,而不是根據所涉及的敘事有多少吸引力和感染力。……這並不是說,針對個人的教牧策略不應該具有同情心,而是說,什麼是同情,什麼又不是同情,這些必須始終根據更深層次的、超越性的原則來判斷。[24]
簡而言之,教會需要回歸聖經。基督教必須有正確的教義和教條。
作爲家庭的教會
人類的自我取決於群體。我們的身份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我們的社交互動建構的。
這意味著,如果教會想要幫助人們找到並保持他們的真實身份,就必須成爲反映和建立在人裡面的神的形像的共同體。教會不應當是宗教狂熱的。它應該是真正人性的家園。它應該是一個家庭。而且應該有一種深深的謙卑,認識到每個聖徒都有其不堪的過去,而每個罪人在基督的王權下都有美好的未來。
那些選擇像公司或教育機構一樣運作的教會確實沒有抓住要點。「弟兄姊妹們」這句話真的很有意義。隨著這世界對人們的真正身份進行誤導,教會將變得越來越至關重要。
* * * * *
[1] 見 Being the Bad Guys, by Stephen MacAlpine, Good Book Company, 2021
[2]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the Sexual Revolution, by Carl Trueman, Crossway, 2020, page 19.
[3] Trueman, 39.
[4] Trueman, 35.
[5] Trueman, 129.
[6] 比較提後 3:2。
[7] 對比太 5:27–30 與羅 8:13。
[8] Trueman, 164.
[9] 提後 4:4。
[10] Storr, 113.
[11] 應當指出的是,如果性是人之爲人的核心,那麼兒童就必須被性化。這就是推動越來越早進行性教育的議題的由來。
[12] Trueman, 219.
[13] 楚曼將批判理論的基本原則總結如下:1)權力可以在有權力的人和沒有權力的人之間劃分;2)西方的主流敘事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建構,目的是維護其自身的權力結構;3)因此,批判理論的目標是通過顛覆其用於證明權力結構的主流敘事,來顛覆這種權力結構。
[14] 這意味著在神學上,現代的觀點可以被歸類爲諾斯底主義的一種形式。
[15] Trueman, 69.
[16] 這就是給人的印象,儘管色情作品經常與抑鬱症、自殺和性販賣有關。
[17] Trueman, 297.
[18] Trueman, 第85頁。
[19] Trueman, 第315頁。
[20] Trueman, 第360頁。
[21] Trueman, 第375頁。
[22] Trueman, 387.
[23] Trueman, 393.
[24] Trueman, 402-403.
譯校:無聲宏揚。原文刊載於九標誌英文網站:Summary of Carl Trueman’s, The Rise and Triumph of the Modern Self: Cultural Amnesia, Expressive Individualism, and the Road to Sexual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