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想探討的是十七世紀中葉特殊(或加爾文主義)浸信會起源的時代……他們決心不惜代價,在上帝有明確命令之處順服上帝;他們認識到,苦難是上帝用來使我們成聖的一種手段。他們還意識到,爲基督的緣故受苦是他們榮耀偉大救主的一種方式。出於所有這些原因,他們會把迫害甚至殉道視爲給教會的禮物。
我想探討的是十七世紀中葉特殊(或加爾文主義)浸信會起源的時代……他們決心不惜代價,在上帝有明確命令之處順服上帝;他們認識到,苦難是上帝用來使我們成聖的一種手段。他們還意識到,爲基督的緣故受苦是他們榮耀偉大救主的一種方式。出於所有這些原因,他們會把迫害甚至殉道視爲給教會的禮物。 與任何環境下的福音工作一樣,南非既有令人振奮之事,也有令人沮喪的事情。作者試通過三個方面的概述來描繪這幅圖畫:教會成員制和教會紀律的實踐、領袖的職責以及神話語的地位。作爲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南非仍然在長期受壓迫的歷史中掙扎……通過對我們國內趨勢的簡要回顧也提醒我們,主的國度確實也正在這裡建立。
與任何環境下的福音工作一樣,南非既有令人振奮之事,也有令人沮喪的事情。作者試通過三個方面的概述來描繪這幅圖畫:教會成員制和教會紀律的實踐、領袖的職責以及神話語的地位。作爲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南非仍然在長期受壓迫的歷史中掙扎……通過對我們國內趨勢的簡要回顧也提醒我們,主的國度確實也正在這裡建立。 因此,一位對神治論和重建派持關切態度的浸信會牧師至少應致力智慧地做這三件事:第一,他研究神治論和重建派的承諾和結果,以確保能準確、誠實地與這一立場進行互動。浸信會期刊是一個很好的起點。第二,他明確闡述浸信會聖約神學以及如何應用它來恰當地區分律法和福音的含義。最後,敬畏主超過一切,他在必要時以溫和和耐心的態度糾正神治論和重建派的錯誤——這都是爲了上帝的榮耀和祂羊群的益處。
因此,一位對神治論和重建派持關切態度的浸信會牧師至少應致力智慧地做這三件事:第一,他研究神治論和重建派的承諾和結果,以確保能準確、誠實地與這一立場進行互動。浸信會期刊是一個很好的起點。第二,他明確闡述浸信會聖約神學以及如何應用它來恰當地區分律法和福音的含義。最後,敬畏主超過一切,他在必要時以溫和和耐心的態度糾正神治論和重建派的錯誤——這都是爲了上帝的榮耀和祂羊群的益處。 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爲《聯會》(Association)的著作從聖經、神學和歷史角度,爲教會有意識地合作提供了令人振奮的理由。該書還列舉了一些實際例子,說明這種合作在今天可以是什麼樣子。
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爲《聯會》(Association)的著作從聖經、神學和歷史角度,爲教會有意識地合作提供了令人振奮的理由。該書還列舉了一些實際例子,說明這種合作在今天可以是什麼樣子。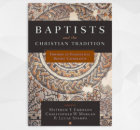 作者介紹了《浸信會與基督教傳統》一書,該書強調了研習神學和傳承偉大傳統的益處——爲了堅固浸信會的信仰。它將使讀者接觸到重要的歷史資料,推動我們更深入地接觸傳統,看到基督教信仰中一直存在的長線。然而在這個過程中,盼望神學檢索把我們引回我們唯一的權威來源——聖經。
作者介紹了《浸信會與基督教傳統》一書,該書強調了研習神學和傳承偉大傳統的益處——爲了堅固浸信會的信仰。它將使讀者接觸到重要的歷史資料,推動我們更深入地接觸傳統,看到基督教信仰中一直存在的長線。然而在這個過程中,盼望神學檢索把我們引回我們唯一的權威來源——聖經。 作者作爲一位聖公會的牧師,從四個方面總結了浸信會教會體制給他帶來的有益的提醒。感謝基督,我們不是因宗派得救,而是因基督得救。健康的教會大公性——即合一,植根於我們對福音的共同信心——這意味著聖公會、浸信會、長老會等之間可以享受團契。即使存在差異,我們也能相互砥礪。
作者作爲一位聖公會的牧師,從四個方面總結了浸信會教會體制給他帶來的有益的提醒。感謝基督,我們不是因宗派得救,而是因基督得救。健康的教會大公性——即合一,植根於我們對福音的共同信心——這意味著聖公會、浸信會、長老會等之間可以享受團契。即使存在差異,我們也能相互砥礪。 作者作爲一位浸信會牧師,列舉了五個他從長老會牧師、教師和思想家身上所學到的寶貴經驗。這並不是說我不能從浸信會的思想家那裡學到這些東西,也不是說我沒有從浸信會弟兄姊妹的教導和著作中學到很多東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我所遇到的長老會牧師、教師和作家的影響,無論是通過親身經歷還是通過他們的著作,我的生活、思想和事工都會差得多。
作者作爲一位浸信會牧師,列舉了五個他從長老會牧師、教師和思想家身上所學到的寶貴經驗。這並不是說我不能從浸信會的思想家那裡學到這些東西,也不是說我沒有從浸信會弟兄姊妹的教導和著作中學到很多東西。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沒有我所遇到的長老會牧師、教師和作家的影響,無論是通過親身經歷還是通過他們的著作,我的生活、思想和事工都會差得多。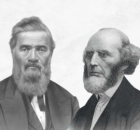 牧師們需要了解,在19世紀,美國浸信會發生了改變。這一改變塑造了我們對歸信、成員資格、洗禮和實踐「重生教會成員資格」的意義這些事情的直覺。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復興主義的直覺和制度化實踐的世界,這些無意中所破壞的,甚至是浸信會的立會之本。通過了解復興主義歷史根源,牧師們將更有能力去批判性地評估今天常常被視爲理所當然的做法。
牧師們需要了解,在19世紀,美國浸信會發生了改變。這一改變塑造了我們對歸信、成員資格、洗禮和實踐「重生教會成員資格」的意義這些事情的直覺。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斥著復興主義的直覺和制度化實踐的世界,這些無意中所破壞的,甚至是浸信會的立會之本。通過了解復興主義歷史根源,牧師們將更有能力去批判性地評估今天常常被視爲理所當然的做法。